斯通纳第一次见到伊迪丝是在密苏里大学院长家的聚会上。她年芳20身材修长五官柔美,高挑的个子穿着蓝色带波纹的丝绸长袍,纤细的手指熟练的侍弄着水壶和杯子,微笑的招待着院长家的客人。她是校董夫人的外甥女,院长的远房亲戚,父亲是一家小银行的行长。 从小学习钢琴,爱好油画和雕塑,气质优雅顺从。当斯通纳的朋友将她介绍给斯通纳时,她答话的声音温柔、羞涩、细声细气,几乎是按照男人们理想中未婚妻标准定制的。为了更加完美她还读过几所女子学校,学习阅读和写作,学做女工、讨论文学,接受着装、举止仪态,淑女用语以及道德修养方面的指点。正是这所有的美好成为伊迪丝不幸人生的根源,她太标准了,标准得无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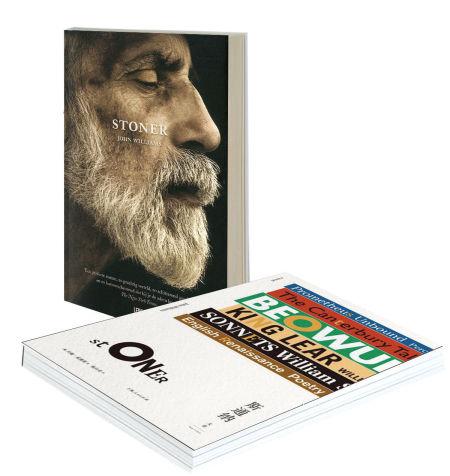
当斯通纳揣着一颗年轻人应有的滚烫的心去追求她的时候,她的矜持表现得近乎冷静。斯通纳说,我能明晚去看你吗?她站在车门口,一动不动,眨了眨眼睛面无表情的说,好的你来吧。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对爱情的狂热憧憬和原始的冲动让斯通纳的表现唐突鲁莽羞涩和不知所措,但伊迪丝却始终保持着面无表情的矜持。在斯通纳准备离开的时候,她又果断的将他留下。这一切在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斯通纳看来都是一位美好得体的女子应有的端庄和礼节。实际上,伊迪丝只是不想错过一次可能的婚姻。毕竟斯通纳终究会是密苏里大学的教授。
“你一定知道我爱你,我都不知道如何掩饰。”当斯通纳表白的时候,她带着几许兴奋的说,“我不知道。我对这事一窍不通。”一个少不更事的年轻人会把这看作做是少女的纯情。但对这一细节的忽略和一厢情愿的假想毁了斯通纳一生。他假想的女神伊迪丝的确对“爱”一窍不通。结婚后,她固执的不让斯通纳插手,收拾新房,擦洗家具,摆弄花草,将小家捯饬的干净整洁。但这并不是基于她对生活的热爱,就像她弹钢琴一样,并不是她喜欢音乐,而是她认为,这是作为一个合格妻子应该做的事情。就像他们第一次做爱,当斯通纳把双手放在她身上,去摸索她背后的纽扣的时候,伊迪丝闭着双眼,嘴唇紧紧抿着,冷淡的推开他,转身背对着斯通纳,动作迅速的脱下礼服,然后平淡的对斯通纳说,你去别的房间吧,我一会儿就准备好了。整个过程,她纹丝不动,眉头紧皱。
散步聊天、收拾房间,所有的日常生活,在伊迪丝看来都是一个合格女人的标准生活,这一切与热爱无关。她在家庭聚会时,神采飞扬、轻松自如的跟客人聊天,在客人面前表现得和斯通纳无比亲密和相爱,但就在此之前半个小时,她冲斯通纳歇斯底里,就因为少了一个晚餐聚会的杯子。她对自己从事文学研究的丈夫的专业毫无兴趣,也从不过问。在女校里学会的绘画雕塑以及钢琴也不过是为了在少女时代增加自己吸引理想未来丈夫的前期投入。

伊迪丝的无趣,让她的英国文学教授丈夫彻底的失望了,他被这种无趣赶到客厅的沙发上睡了。正如伊迪丝非常确信的,他是不会为了所谓美好的真正的生活而和她离婚的。这不是夫妻之间通常有的冷战,战争是需要利益冲突引导的,他们之间没有。直到斯通纳经常将一群学生带到家里讨论的时候,她意思到自己在一群人的谈笑风生中备受冷落的时候,她开始反击,她用自己少女时代训练有素的本领,去参加组织戏剧社,把戏剧社的朋友们带到家里聚会,将丈夫逼到学校办公室后,她便厌烦了戏剧社。
结婚的第三年,伊迪丝觉得他们应该要一个孩子,这并不是她喜欢孩子,只是因为孩子是一个标准的家庭应有的。孩子出生后,她也曾尝试着去爱自己的孩子,她叫斯通纳把孩子抱过来,她看着自己的孩子就像看一个陌生人,厌倦的叹口气,就把孩子递给了斯通纳。洗尿布、哄睡觉、喂牛奶、洗澡,给孩子挑选衣服,破了后缝补,这些事情都是斯通纳做的。她对斯通纳说,“不管我在哪儿都能听到你的声音,听到孩子的声音,而且还有气味,我受不了那气味!一天又一天,那尿布的气味,还有,我受不了,我又躲不掉那气味。”斯通纳更像一个母亲而不是父亲。伊迪丝本可以将对孩子的这种漠不关心维持到孩子成年后离开这个家,但是当孩子开始和父亲在书房里自在开心的聊天、玩耍和学习的时候,伊迪丝再次觉得自己被冷落。她开始冲着孩子大嚷,“格雷斯,你父亲要工作了。别打扰”。在斯通纳一再强调,孩子并没有打扰自己后,她仍然冲着孩子大喊,“格雷斯你听见我说的吗?赶快出来。”
伊迪丝的不幸在于她的内心没有爱,但是她不允许周围的人相互爱着对方。这种爱不只是人与人之间的爱,还包括对各种事物的爱。她是一个无趣的女人,最开始的时候斯通纳将这种无趣错误的理解为女孩子的端庄和矜持。这个可怜的女人,当她得知自己的丈夫与别的女人相爱、偷情的时候,可以长时间的保持冷静的观望,直到她的情敌被迫离开斯通纳。她只是在必要的时候,像恶作剧一样的拿出来取笑一下自己的丈夫。最终当她的冷嘲热讽斯通纳似乎并不在乎的时候,她开始厉声诅咒,故意在丈夫看书的时候,疯狂的敲击她并不喜欢的钢琴,在女儿和丈夫说话的时候,突然对他们大声叫嚷。
伊迪丝四十岁的时候,仍然像少女时一样削瘦,透着一种坚硬、脆弱、不屈不挠、满怀怨气。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